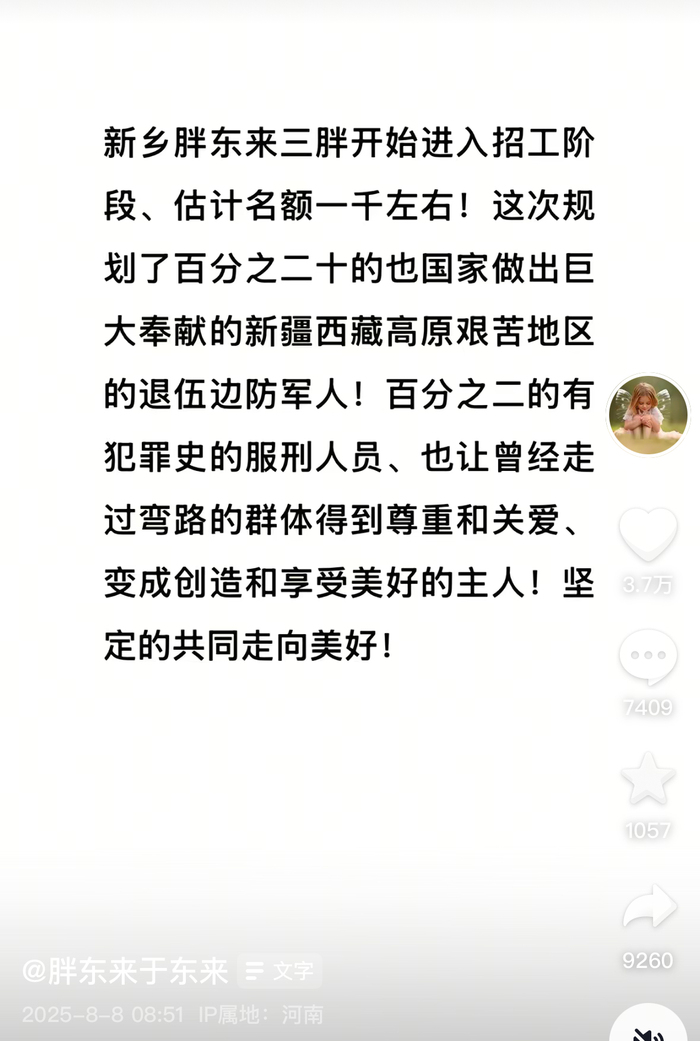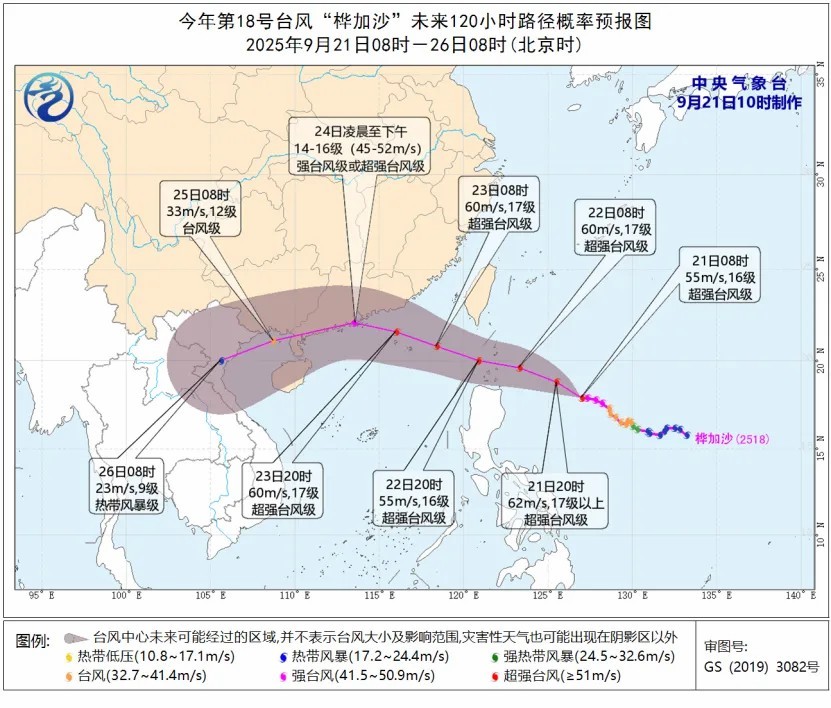《邓南遮占领阜姆自由邦》——媒介力量下的历史复现
2025年6月,上海国际电影节圆满收官。在其展映的数百部电影中,一部来自克罗地亚的纪录片《邓南遮占领阜姆自由邦》(Fiume o Morte! , 2025),凭借其独特的影像风格,以及背后蕴含的深刻主题核心获得了观众的认可。早在今年1月的鹿特丹国际电影节上,本片的艺术价值就被广泛褒奖,并一举夺得了该电影节的最高荣誉——金虎奖。鹿特丹国际电影节向来以支持各地的新锐导演而闻名全球,其主要关注电影的两大特性:“实验性”和“反叛性”,而《邓南遮占领阜姆自由邦》则是两者兼具。本片开创性地将当下演绎与历史影像相结合,复现了一场百年前的政治闹剧,并由此与当下的政治生态发生连接并给出警示。评委会在对该片的授奖致辞中明确指出:“在当代欧洲极端民族主义(ultra-nationalism)兴起......”,这也点出了在当下,这部以历史为题材的电影所不可忽视的现实启示意义。

《邓南遮占领阜姆自由邦》海报
《邓南遮占领阜姆自由邦》的故事发生在导演伊戈尔・贝齐诺维奇(Igor Bezinović)的故乡里耶卡(Rijeka),旧时称作阜姆(Fiume)。本片的制作团队在当地邀请普通市民与他们一起参与一场历史复现,通过他们对1919年意大利诗人、贵族兼军官加布里埃尔・邓南遮(Gabriele D'Annunzio)率军占领阜姆自由邦的全过程表演,并搭配历史影像和口述旁白。揭示了以邓南遮为代表的法西斯式政治的危害以及其媒介力量对公共记忆的侵入。唤起公众对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等议题的思考。
电影采用由浅入深的叙事逻辑,整合大量史料影像与旁白解说,高效帮助观众构建了 “阜姆自由邦” 的历史背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奥匈帝国解体,其边境城市阜姆随即被战胜国分割,协约国的政治首脑在该城市归属问题上始终难以达成一致,既无法确定将其划归意大利王国,也未能明确是否交由新成立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后发展为南斯拉夫王国)管辖。同时,阜姆的市民也面临着严重的民族认同、身份与立场选择的撕裂,亲意大利的士兵及民众,与亲南斯拉夫的士兵及民众之间,持续发生各类冲突,不同阵营间的摩擦很快演变为流血事件。协约国高层随即要求意大利军队(具体为撒丁掷弹兵(Grenadiers of Sardinia))撤离阜姆,此后,亲意大利阵营的军队与民众,不断寻找着一位能带领他们重回阜姆的领袖。
在阜姆的统治真空期局势混乱之时,加布里埃尔・邓南遮趁机登上政治舞台。他先率百余名意大利士兵进驻阜姆(后队伍扩至数千人),随即宣布占领这座自由邦。影片以戏谑手法还原这一事件:普通市民扮演的邓南遮爬上山坡弹着吉他,在其激昂的音乐中,数十辆象征武装军车的现代卡车缓缓驶入里耶卡。这一幕开启了历史复现活动,数百名里耶卡市民共同演绎了邓南遮统治阜姆自由邦的 16 个月历程。
影片开篇时,导演向里耶卡市民采访:“您知道谁是邓南遮吗、他对里耶卡做了什么事?”,而后一连串的回复便密集地出现于银幕之上,迥异的答案立刻构建起了一段模糊的公共记忆。而紧随其后,对历史影像的解读则是通过导演和市民们的口述展开,形成了一种官方对公共记忆的入侵,区别于传统纪录片一以贯之的官方叙事,本片让话语权再次回到了以市民为代表的集体手中,通过历史复现行动完成了一场“记忆-影像-复现”的线性串联。
电影运用了极具开创性的手法构建起整个行动,尽管本片仍然遵循以时间为主的线性叙事,但大量历史影像搭配着市民的共同参与创作,从而形成了多重的叙事主体。影片反而精准地揭示了历史影像的空洞性,从而达成一种反讽的效果。由于同一场域在过去与当下有不同的名称,下文中将以“里耶卡”指代当下的城市,而“阜姆”则指代过去的城市,以此区分历史影像与当下演绎空间。

《邓南遮占领阜姆自由邦》剧照
影像复现与史实再阐释
影片呈现邓南遮和支持者占领阜姆自由邦时,常用历史影像结合现场演绎,有时还会 “画面并置”。导演伊戈尔说,这部电影非常依赖档案也遵循史实。他希望 “一切都基于档案、基于事实”。另外,非专业市民的演绎能消除档案电影(Archive Film)里常见的压抑和肃穆。他们在城市中精确复刻历史照片和影像,而导演也保留了他们笑场、走神、口误等镜头,这些都使得影片有别于传统纪录片,更欢快、更滑稽地表达了讽刺。
这种常把历史场景“移植”到现在的拍摄手法,构建出一个以“里耶卡市民”为叙事核心的历史再阐释视角。电影中有一段:当邓南遮刚进阜姆,在总督府阳台演说时,电影插入历史影像,显示出万人空巷的阜姆。但现实里的里耶卡却只有演员的两位家属为其鼓掌。这种“画面并置”在电影里反复出现。比如在现在的商业步行街重现阜姆的阅兵,历史影像里有成百上千整齐的军团士兵。但现实的里耶卡,只有几位路人误闯镜头,缓慢走过。
德国电影理论家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解释过“再现”的独特之处:摄影和记忆图像能够关联,是因为它们总跟特定主体的真实内容联系紧密。但“再现”会用完全外在的机械方式接管这种主观视角,决定现在和过去的复杂关系。
在这部电影里,历史复现就是对物质现实的“再现”。这给了影像一种新权力:对抗官方的历史解读和意识形态。个体能通过这些新影像进行私人的表达,当代表达的重要部分,就是私人记忆和官方话语之间模糊的场域。
因此,导演依靠非专业市民的粗糙演绎,完成了一出反讽英雄叙事的戏剧。同时,他也通过历史复现,完成影像的当代表达和对史实的再阐释。另外,在现在的原址再现历史影像,不只能提供可参照的相同空间,还能靠这个空间呈现法西斯仪式的空洞和表演性质。
影像的意识形态呈现力量
不难发现,在上述一切呈现的先决条件中,当代表达和画面并置的空间都高度依赖于大量历史照片和影像的留存。邓南遮很早便察觉到影像媒介的重要性,也明白该如何借助其传播政治理念。1919年时,摄影技术还尚不常见,邓南遮却主动邀请了大量摄影师为他记录,导演伊戈尔称其是“最早真正理解媒介的力量以及如何运用媒介来呈现政治理念的人之一”。

《邓南遮占领阜姆自由邦》剧照
在占领阜姆期间,邓南遮营造了一种“政治壮观”(politics of spectacle),其中包括了阳台演讲、罗马式敬礼、群体仪式、戏剧化群众动员等元素。这些做法均被墨索里尼效仿,为意大利法西斯奠定了重要模板,邓南遮也因此被称为“意大利法西斯的约翰·施洗者”(John the Baptist)。邓南遮在阜姆起草并推动的《卡纳罗宪章》(The Charter of Carnaro) 也预示了后期法西斯政权的若干政治纲领。作为一位原始法西斯主义者(proto-fascist),邓南遮用浪漫主义方式重塑了政治空间,使他成为研究早期法西斯主义与意大利收复主义(Italian irredentism)的重要案例。
他对音像媒介的高度敏感也影响了现代政治影像的发展。邓南遮擅长利用影像推广他个人的意识形态,这于是启发了后世将电影运用在现代政治影像领域,例如纳粹的宣传影片《意志的胜利》(Triumph of the Will)就大量运用群众集会、游行以及各类华丽的仪式性动作,把领袖叙事融入集体神话。这种影像的呈现方式也标志着电影开始参与历史与意识形态的建构。
邓南遮留存下来的大量影像资料,先是揭示出视觉媒介在历史叙事和政治宣传中的关键地位,其次也显露出了意识形态对影像内容的筛选。在与他本人相关的历史事件中,标志着他广得民心的抵达阜姆的照片被完整保留,而公众投下反对占领的投票却被他派兵捣毁投票箱的照片却无一保存,影像的倾向性在此时便显得格外明显。

《邓南遮占领阜姆自由邦》剧照
纪录片的创作通常要遵循史实,本片也通过穿插历史影像和当代演绎来避免过度戏剧化的“再现”过程。但唯独有两个场景,影片通过高度写实的方式幻想性地重现了历史原场面。其中之一便是上述的士兵干扰公投场景,导演安排了多种角度的拍摄和黑白照片的滤镜,以确保在里耶卡进行演绎的场景可以构成仿古式的照片。这种伪造的历史影像区别于影片先前在当下空间对影像的复刻,意在表达对官方叙事中空缺的不满,对抗了意识形态对历史影像的审查,并透过媒介力量填补了个人记忆与官方历史间的模糊空间。
青年士兵的身体表演
另一处关键的对历史场面的仿古式重现便是出现在电影的结尾,在邓南遮执政的末期发生的“血腥圣诞节(Bloody Christmas)”事件,包围阜姆的意大利军队奉命与城内的军团士兵交火,导致数十名军团士兵死亡。而通过历史复现,导演将镜头对准了死亡士兵们的伤口与摄人心魄的死相。士兵的死亡场景当然是由里耶卡的市民扮演的,与电影其他的演绎场景不同,显得格外肃穆与庄重。导演用死去的士兵身体作为表演的主体,表达了对荒唐政治而带来的无辜死伤的抗议。这也让我们得以深究影片的一大细节——青年士兵的身体表演。
纵观全片,无论是历史影像还是当下的演绎现场,影像的主体只聚焦于邓南遮还有其成百上千的军团士兵。导演伊戈尔透过本片意图讽刺邓南遮的领袖形象,提供历史事件的再阐释方法,这也让这些本属于法西斯英雄叙事之外的普通士兵变成了叙事的主体,而他们的身体表演也成为了解读本片创作意图的重要线索。
电影中,导演直叙了选拔军团士兵扮演者的方式,要求懂得拳击,有力量感的青年市民。而在影片的后段,我们跟随旁白念出的邓南遮军团的士兵守则,看到了里耶卡市民对其的演绎:大量的士兵赤裸上身训练、叼着刀露出凶相,甚至是杂技。以此还原了历史影像中“英雄式军团”的集体形象。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在《规训与惩罚》中提出的“支配肉体的政治技术学”点出了邓南遮大量留存军团训练影像的原因。福柯指出权力会通过控制、干预和训练肉体,使其完成特定任务、或表现某种仪式。邓南遮意图塑造出一副充斥着训练有素的健壮肉体的集体形象作为其拥趸的象征。
青年士兵的身体让这种政治力量视觉化,也具象化了邓南遮受到广泛拥护的地位,在法西斯叙事中也借助这种集体力量提升了领袖的个人魅力。而里耶卡市民所扮演的士兵在集体力量的演绎中充斥着夸张和不协调的表演,也是对这一历史影像具有表演性的最好讽刺。
而最终,历史复现行动以士兵的惨死作为收尾,影像的呈现从健壮的集体形象变化为扭曲死亡的个体面貌,这一对比也使得身体在政治表达的功能中从“展现强盛”变成了“见证毁灭”,而拍摄主体的变化也蕴含着导演所意图展现的意识形态变化,从法西斯式的集体主义迈入当代更为强调的个人利益,也是对历史和社会价值观变化的回应。

《邓南遮占领阜姆自由邦》剧照
以桥梁为界的历史回望
在本纪录片中,导演用各种技术手段和呈现方式对邓南遮历史事件的复现,超越了民族主义的叙事逻辑,成功地将讽刺对象扩张至法西斯式的英雄神话(heroic myth)与个人崇拜。然而,当电影迈入尾声时,导演的自述却不可避免地让影片的批判核心,再次回归了个人的文化生活经验以及民族与身份认同之中。
在他的叙述中,对邓南遮的评判被简单地划为了二元对立(binary opposition)的民族叙事,即在意大利他被认为是爱国者、但在克罗地亚则是侵略者和法西斯分子。这种从民族主义视角出发的,对邓南遮人物解构的简化方式,实则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中所述的民族认同的排他性如出一辙。也正因如此,影片失去了对意识形态和历史人物的探索,更为复杂的视角和解读空间的可能性。也最终使得电影无法摆脱其克罗地亚立场的“政宣电影”色彩和斯拉夫民族背景。
影片最终的立意也无法被升华至一个更普世的问题:即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多次分裂和重组之后,我们究竟该如何通过政治和历史研究应对族群分裂和历史创伤的跨代际影响?
《邓南遮占领阜姆自由邦》通过对历史影像的复现,还原了一个世纪以前的荒诞统治。导演通过当下空间的非专业表演,反讽了以邓南遮为代表的法西斯领袖叙事,以幽默的方式揭露了其空洞性和表演性,也抨击了意识形态作用之下那具有强烈政治目的的历史影像。影片也由此提醒观众,也应该对一手的历史资料保持审慎,不容忽视政治干涉下的媒介力量。
而在人物的塑造上,青年士兵则被功能性地认定为表现强健和对领袖的忠诚视觉工具,其作为集体的大量训练和行进影像只是用于政治宣传,而当其价值随个体的牺牲而消亡时,影片以最写实的方式呈现了死亡。以此对当代政治举出前车之鉴,向观众传递出:“不要让荒唐的政治再次出现,以至于让年轻人付出无辜的死亡”的警示。
电影的开头和结尾选用了同一类型的空镜:横穿城市的河流以及架于其上的桥梁,导演伊戈尔希望这种设计能让观众明白桥梁的重建是因为曾发生的侵略行为。这种设计不仅仅是指出城市中依托桥梁的空间连接,更是对历史与当下、记忆与现实的连接,里耶卡居民始终得以以桥梁为界,获得一个回望阜姆历史的机会,并将这种记忆和警示永存心中。
文献:
IFFR授奖词,Links:'Fiume o morte!' Wins Rotterdam Tiger Award
讽刺对荒诞:采访《邓南遮占领阜姆自由邦》导演 Igor Bezinović,纪录公社,links:讽刺对荒诞:采访《邓南遮占领阜姆自由邦》导演 Igor Bezinović
《历史:终结之前的最终事》,Siegfried Kracauer
《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Michel Foucault
《想象的共同体》,Benedict Anderson
加布里埃莱·邓南遮和意大利政治的审美化, Victor Biryukov,links:加布里埃莱·邓南遮和意大利政治的审美化
克拉考尔的“羊皮书”:蒙太奇、现实与历史书写——重读《电影的本性——物质现实的复原》,孙柏,links:孙柏︱克拉考尔的“羊皮书”:蒙太奇、现实与历史书写——重读《电影的本性——物质现实的复原》(电影的本性)书评